2019年末時因為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轉換,內心湧起一股莫名的不安,想做點什麼來消弭卻又不知道能做什麼。反覆思考時認知到生活經驗的貧乏讓我對周圍事物的感受非常扁平,在和朋友分享煩惱的過程中得到了一個靈感—我可以透過閱讀來提升感知與意識。
文字是人類記錄體悟的方式,是關於我們生活在世上感受到的一切,包括愛、恨、樂、苦、生命、死亡、道理、無常。將文字集結成冊的書籍,就是社會現象的載體,透過閱讀其他人曾經有過的體驗,就能與他人產生更多交集。我們得以融合自身的經驗與書中觀點,把人事物看得更真切,經由自省塑造更堅實的涵養。
閱讀是與作者對話來培養思維的彈性與可容性,使我們困擾的大多數時候並非人事物本身,而是我們對於其的看法,但改變人事物本身的難度高得令人畏懼,我們力所能及的通常是改變自己的觀念。
提升自我意識便能以不同的視角「詮釋」,即使面對同樣的狀況,人的感受仍會因詮釋的方式而不同。若能理解立場相異的群體,領悟是與非皆有各自的道理,就像明白每個人的樣貌迥異一般,跳脫凡事都得順我意的框架,便不會陷於主觀的成見而感到痛苦(那個人這樣做真是對我不公平;我的想法是對的,那件事情應該照我想的發展)。《莊子.內篇》〈齊物論〉,「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,則莫若以明」,就是指這種心境吧。
「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,則莫若以明。」
如果想看見自己覺得不對的事物的肯定面,反省自己覺得對的事物的不足,不如站在太陽和月亮的高度,公平照看大地上的萬事萬物,當你可以無所偏執地同情、體諒每個不同的立場,完整照見一件事物的各個不同面向,世間的真實將更加清晰地呈現在自己面前。
以上白話譯文摘自蔡璧名所著《正是時候讀莊子:莊子的姿勢、意識與感情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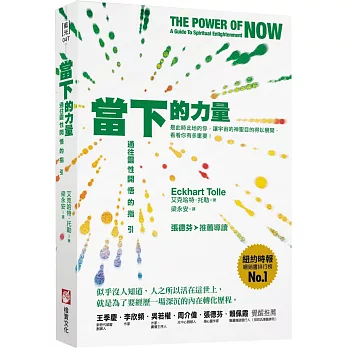
思維的改變需要足夠強大的刺激,通常經歷逆境能迫使我們轉換思維,但除了那種「不得不」的狀況之外,有更簡便的方式獲得刺激,我認為閱讀便是提升自我意識成本最低的方式。
就像前面提及的,感受到自己的人生見識已經不足以讓我切換視角看待周圍人事物,總是人云亦云,無能解讀週遭的事件、人生的變化與自己的心境。這個體悟成了動機,使我養成了閱讀的習慣。每天利用零碎的時間至少閱讀半小時,2020年到2023年平均一年讀完55本書。空閑時間最多的大學時期都沒這麼認真讀過書,以前讀書是被逼著,現在則是受內在驅力推動著。
我對閱讀材料不設限,只要能勾起興趣的便會找來讀,但我會盡量跳脫閱讀舒適圈,接觸自己不熟悉的領域。廣泛閱讀更能擴張視野,畢竟這是我培養閱讀習慣的主要目的。
閱讀時我會在筆記本記下認為有用的段落,我相信那些文字會在將來提供出乎意料的幫助。在現代還選擇用紙本記錄,是因為眼及手的協作能增加輸入的刺激,深化大腦對於書中內容的記憶。但為了方便搜尋,我會在整本書閱讀完畢後將紙本的筆記一一輸入雲端的試算表。若書中沒有特別值得記錄的文字,我仍會用心智圖彙整內容,便於事後回憶。
人生沒有無用的經驗,也沒有讀了無用的書。
我時不時便會瀏覽閱讀筆記,希望那些書中的智慧能帶給我處世的靈感與啟發。
人的關注對象十分受自身感受和想法的影響,當我心裡覺得缺少什麼或對於什麼有困惑時,總會遇見那本恰好打進心坎的書。
《當下的力量》(The Power of Now)便是在我因為父親的價值觀而感到痛苦、迷惘時,指點方向的燈塔。
和父親的關係在學生時期大致維持著不冷不熱的關係,從比較有記憶以來他就因工作長期待在中國或越南,他打電話回家的頻率低,在通訊軟體普及後也沒有增加多少聯繫。而即使回台也僅是短暫停留幾天,所以並沒有和他建立深厚的感情基礎。不過年輕時對家人的思念和情分仍然在心中佔有優勢地位,足以讓我忽視父親根深柢固、與我抵觸的價值觀。
而出社會後接觸的人事物多了,有了各種比較對象後,漸漸感受到父親的確散發出令人不舒服或說不自在的氛圍。他的神情、肢體、語氣、用詞,再再都讓我察覺到他的不快樂,他對週遭環境的不滿、對身旁人們的不滿、甚至對人生的不滿。他無意識傳遞出的負面情緒,讓我想到要和他對話或互動時內心總會產生抗拒。
抗拒的同時也總是困惑,為何父親會有那種源於「言行不一致」的異樣感?
為什麼身為創業者的他,擁有比一般人多的資產餘裕,有所謂「成功人士」的各種象徵物,內心仍像有什麼遺憾般,那麼地不快樂?為什麼從小到大總是跟我說「一定要快樂」、「快樂才是最重要的」父親,總是眉頭深鎖?為什麼情緒總像是隨時要沸騰的茶壺一樣,任何不順心的小事情都可以讓他瞬間就爆炸?為什麼十句話有八句話都在批評、都在發表高見,不接受他人的想法?為什麼總是說「等我『之後』回去『再』給你什麼」,從不說能立即為家人做什麼?而那個「之後」來臨時,卻總是食言?
父親的言行對我而言十分費解,曾經和他有過的這番對話,讓我的疑惑更加深了。
「爸,你認為快樂很重要,你追求快樂這麼多年了,你覺得自己快樂了嗎?」
「沒有,還是不快樂。」
他的回答讓我感到挫折,那個揮之不去不順暢的感受卡在心頭好一陣子,那時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他追尋「快樂」幾乎一輩子,「快樂」仍舊離他如此遙遠,而他似乎完全不理解自己嘴裡發出的「快」、「樂」這兩個字組成的詞彙所代表的真義。
直到讀了《當下的力量》(The Power of Now),我才明白困住他的是什麼—是內在的時空和對幸福快樂的定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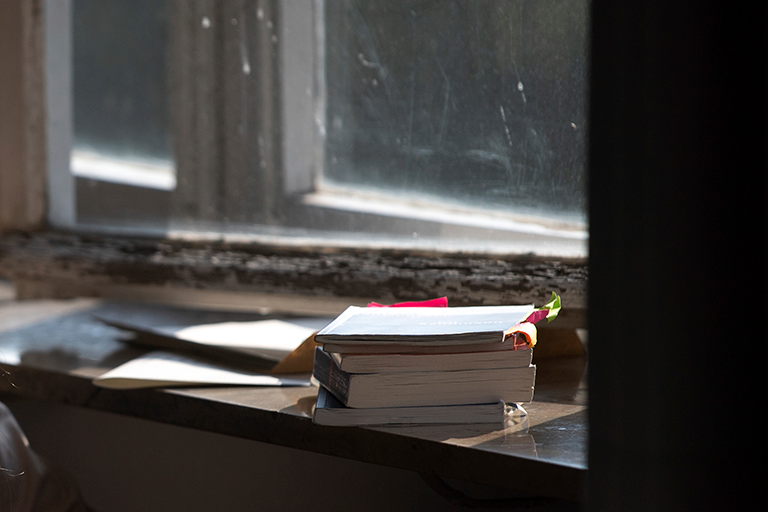
「我思故我在」,一般人認為心智活動正是代表自我的存在,但《當下的力量》(The Power of Now)作者艾克哈特・托勒(Eckhart Tolle)認為把自我等同於思考是謬誤。他提出的觀點是—在腦中不間斷叨叨絮絮的消極、負面話語,是「小我」(ego)在自言自語—「小我」讓我們總是無意識地、不斷進行強迫性思考,因此使腦中充滿喋喋不休的噪音,批評、比較、猜忌、抱怨、欲望,其實都是「小我」在喃喃自語,而不是「真正的自我」(true self)。「真正的自我」是能夠意識到美、愛、創造力、喜悅,達到內在平安的。
若我們認同了「小我」製造出的虛假自我,就給予了「小我」牽制住內心的力量。「小我」不停地在腦中發出聲音,讓我們錯誤地透過那些負面感受建構自我認同,讓我們以為自己就是欲望、執著、厭惡本身。
「小我」是在個人及文化的環境下塑造成的一種自我感,它非常依賴外在認同,像是「擁有物、工作、社經地位、教育水準、外貌、特殊才能、關係、個人與家族史、信念、政治認同、國籍認同、種族認同、宗教認同,和其他的集體認同等」,若不餵養「小我」這些外界物質,它便會使情緒起伏擺盪,它讓我們以為取得這些就等於幸福快樂。但事實是,即使取得這些外在條件,內心仍不得安穩,因為它們帶來的快樂十分短暫,總是稍縱即逝,因此需要不斷地追尋,感受那曇花一現的快感。
「小我」還有一個特質是,它只活在過去與未來。
它會不斷叨絮過往發生的事情,為的是讓過去保鮮,它會用「沒有了過去,你會是誰?」、「要不是其他人過去對你做了什麼,你也不會淪落至此」來蠱惑。「小我」讓我們以為過去充滿了力量,足以支配一生,但其實那個力量是我們自己賦予的。
它還會讓人以為幸福只存在於未來,使我們不斷說服自己:「只要等到那一天,等到這件事或那件事發生,我就會更幸福了」。
內疚、後悔、怨尤、哀傷、難過、痛苦,是因為我們過度關注過去。不安、焦慮、緊張、壓力、擔憂,是因為我們過度關注未來。
只要人生受到「小我」控制,就得不到真正的安適自在,「小我」讓我們忙著追憶過去、追逐未來,它不在乎最重要的「當下」,但其實我們唯一握有的就是「當下」。

「小我」製造的負面思維日積月累佔據身心,形成負面的能量場,作者稱之為「痛苦之身」(pain-body),痛苦之身的食物是憤怒、破壞、憎恨、哀傷、暴力、疾病等所有情緒張力。作者把痛苦之身形容得很具象—有的痛苦之身就像哭鬧不停的孩子,有的則有肢體暴力、情緒暴力傾向,有的會攻擊身邊的人,甚至攻擊宿主(你自己)。原本熟識的人一旦存在他體內的痛苦之身被喚醒,會覺得他突然變得好像不再是他了。
「小我」希望我們藉由痛苦之身創造出一個不快樂的自我,並且把這個虛假的自我當成「真正的自我」,於是我們便會因為害怕失去自我,寧願活在痛苦之中,也不願失去那個不快樂卻熟悉的自我。
我的父親就是被「小我」攫獲的人。
快樂及任何美妙的體驗就如同其他情緒,來來去去,是短暫存在的狀態。始終不變的只有內心的自在平安。但他以為快樂是一種永恆的狀態,以為只要得到金錢、地位等所有身外之物就能維持快樂的狀態。若得到之後仍不快樂,僅是因為還不夠多,未來他就能得到更多。但度過無數個未來了,他仍舊無法達到自己定義的「永恆的狀態」。
他認為所有的幸福快樂都存在於未來,「當下」只不過是未來的跳板。
事實是,受「小我」控制便不可能感受到平靜或滿足,頂多在追尋到渴望之物時,得到短暫的滿足感。
當父親說他依然不快樂,是因為他錯誤地定義了快樂。快樂不是握在手裡不會消逝的東西,而是充滿在所有生活的細節之中,我們要思考的不是如何追求快樂,而是在生活中發掘快樂,只要我們靜心感受,便能在專注於工作時、與朋友聊天時、與家人用餐時意識到快樂存在於「當下」。
長遠快樂最重要的因素,是我們和家人、好友、群體的關係。但關係的經營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暴十寒的投入,它是「重要但不急迫」的應辦事項,若不願意有意識地每天花時間在上頭,而總是空泛地承諾「未來我會給你過好生活」、「未來我再載你四處旅遊」,當那個未來時刻來臨時,會發現自己身邊已經空無一人了。
《領導的黃金法則》裡頭有個段落讓我很有共鳴:
「把人生想成一場遊戲,你拿五顆球,個別命名為工作、家庭、健康、朋友及靈性,你丟球在空中拋耍,不能讓它們墜地。你很快就明白,『工作』是顆橡皮球,如果你漏接,它落地後會再彈起來;但其他四個球—家庭、健康、朋友及靈性是玻璃球,如果你漏接任何一顆,它們不可避免會有磨損、擦痕、裂痕、缺角,甚至完全碎裂,再也不會完整如昔了。你們必須明白這一點,並竭力保持生活平衡。」
父親似乎不怎麼放心力在感受與意識身心內在,他不知從何時開始就不再活在「當下」了,他所談論的總是「未來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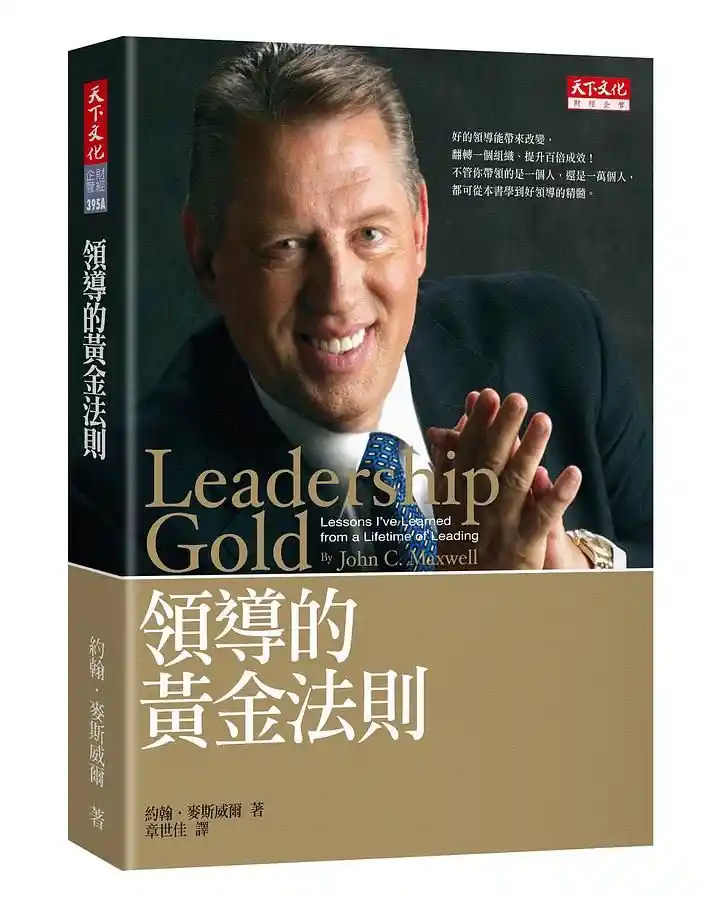
從我6歲開始他就在國外生活,直到現在我已經30好幾了,他還是在說「等我回台之後我會再如何如何」云云。曾經以為他會兌現承諾,但好幾次希望落空之後,我自然學會不把他說的話當真了。雖然不再因此受傷,但和他的心理距離變得非常遙遠,遙遠得當我結婚搬離家後,我是鬆口氣而不是哀傷。離開原生家庭,讓我減輕了許多心理負擔,再也不用因為父親沒有意識地陷於「刺蝟困境」(Hedgehog’s dilemma)而感到糾結。
我可以明確感受到他想與家人親近的心,但他的痛苦之身經常顯現,十分易怒又容易哀傷,因為無法抑制情緒膨脹,在事情不順時總對他人苛刻,讓人想和他靠近,又怕被他刺傷。
曾經想過是否應試著改變和父親的關係,但當兩邊的意識差距太大,要重新建構良好的關係簡直難如登天,於是我只能努力調整自己的視角,像是透過《當下的力量》(The Power of Now)來理解父親。但與父親相處時內心產生的抗拒感受,並無法因為理解而稀釋太多,於是我只好選擇遠離,唯有把自己與他散發的毒氣隔離,我才能避免驚擾沉睡在內心的痛苦之身。
作者教我們擺脫痛苦之身的方法是—保持臨在,臨於「當下」,當個沉默的觀看者,持續觀照自己內在、想法與行為,全神貫注觀察「小我」固有的思維模式和慣性。不要專注於痛苦的情緒,而要深度覺知自己正在觀看著「想法」,認出那就是痛苦之身。認出時不要去思考,不要讓那些感受轉成思維,不要去評斷或分析,不要透過它建構自我認同,接受它就是這樣的存在。易怒、沒耐性、憂鬱、想傷害別人等,即是痛苦之身正在甦醒的徵兆,我們要在它從休眠狀態甦醒那一刻就逮住它。
逮得住它,我們便能擺脫「小我」的箝制,啟動一種更高層次的意識,「我們對腦中的聲音變得能一笑置之,如同面對孩子的童言童語,不再對心智的一切如此在意,我們的自我意識擺脫了對它的依賴」。
當我又因為不可避免地與父親接觸而感到沮喪時,我會馬上觀察它,只要意識到自己正在觀察,便不會讓情緒過於洶湧以至於淹沒了自己。我也將曼德拉(Nelson Mandela)的格言放在心底,當「小我」開始告訴我要去埋怨、憎恨時,我會提醒自己:「留住怨恨,就好比自己喝了毒藥,卻期望敵人會被毒死。」(Resentment is like drinking poison and then hoping it will kill your enemies.)
從小父親就把「快樂」掛在嘴邊,我隨著年齡增長,漸漸對他口中的「快樂」感到困惑,於是某種程度這成為了我心中的議題。除了《當下的力量》(The Power of Now)我還讀過幾本談及幸福快樂的書,像是《象與騎象人》(The Happiness Hypothesis)、《為什麼我們拚命追求幸福,卻依然不快樂?》、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?》、《子彈思考整理術》,每本書都有交集之處,但我認為《當下的力量》提出的觀點最完整、最具說服力,帶給我的影響也最具體。

我們常常游走在過去與未來之間,卻忘了我們的能動性唯有「當下」才能發揮,這本書讓我領悟到,真正該為自己內在負責的是自己,過去和未來的力量永遠不可能凌駕於「當下」的力量,唯有全神貫注於「當下」才能體會真正的平安、喜悅,才能從對於過去的悔悟和對未來的期待中得到解脫。
書籍,是作者將對於特定議題的體悟凝聚而成的結晶,當遭遇困難、挫折時,有著難以言喻的苦惱時,我總是向書籍求解。陷入充滿個人性的煩惱時,就讀宏觀的歷史、總體經濟;對自身感到矛盾時,就讀社會學、心理學;對人際關係感到棘手時,就讀處世哲學、自我成長。每本書都是我的解答之書,文字能帶給我與人對話時無法獲得的慰藉。
※首圖(圖片來源/摘自 Thought Catalog on Unsplash)
※延伸閱讀:逆思維雜談,重新思考有多重要?
